将禁令、规范、公文、契约和讼案等铭刻于青铜器或石碑上,公布彰显,以备考察,以垂久远,是中国古代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传统。多年来,法律碑刻并非没有研究者,只不过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些名碑,缺乏系统性。1998年,李雪梅调入古籍所,很快便认定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做”的研究方向,此后心无旁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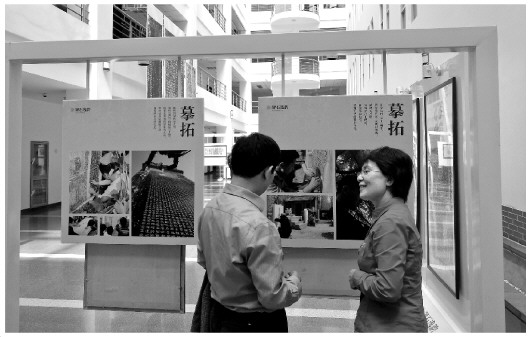
图为碑石逸韵:古代法律碑刻拓片展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李雪梅(右)与一位观展者交流。
“咱们就在这儿聊吧。”5月2日上午,阳光洒进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逸夫楼一楼展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李雪梅微笑着,把双肩包放在一边,柔声说道。于是,展厅边的木质平台上,一场席地而坐的采访开始了。
展厅陈列着自汉代以来主要朝代的29种拓片和刻石。其中,14件展品为李雪梅和她的学生们所亲手摹拓。作为这场“碑石逸韵:古代法律碑刻拓片展”的展品提供者,李雪梅显然对每一位参观者饶有兴趣。视线穿过展板间的缝隙,她不时地发现熟面孔,之后便起身打招呼。其中,有人完全是因为观展才结识的,这让李雪梅觉得很欣慰:“真是发现不少同道中人,也觅得了几位知音。”而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研究领域,她脱口而出的是——高冷。
18年寻获八千法律碑刻线索
将禁令、规范、公文、契约和讼案等铭刻于青铜器或石碑上,公布彰显,以备考察,以垂久远,是中国古代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传统。多年来,法律碑刻并非没有研究者,只不过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些名碑,缺乏系统性。1998年,李雪梅调入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很快便认定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做”的研究方向,此后心无旁骛。十几年来,她亲访碑石,遍览志书,掌握了七千九百余种古代法律碑刻的线索,并将这些碑刻的基本情况汇成一部《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序录》,作为考察核实工作的“秘籍”。
许多人研究碑文多是通过研读史料,但李雪梅却更注重实地访碑,以搜集第一手资料为要务。她说,这也是古代金石学家一贯的传统。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前两天,她刚风尘仆仆地从河北回京。一块五代时期的法律碑,是她此行的牵挂所在。据文物志记载,这块石碑就在曲阳“燕川村南1.5公里的慧炬寺遗址”。然而,去到当地才发现,燕川村早已经分为东西两半,这无疑加大了寻觅难度。反复向村民打听,慧炬寺遗址几乎无人知晓,古碑的线索更无从追溯。问了十几个人之后,终于有了大致方向,但慧炬寺遗址距离远近说法不一。苦于遗址地处偏僻,村庄又在修路,迂回绕行,没有向导,难以找到。终于,劝动了一位老人指路进山。待费尽周折找到遗址,却发现所寻觅的那块法律碑早已不知去向,一行人只能抱憾而归。
类似这样访碑而不得的经历,穿插在李雪梅的研究过程中,让她总有种紧迫感。“再不记录下来,很多重要的资料就看不到了。”
师生共同自学古老拓碑技艺
研究之初,李雪梅用拍照的方式记录碑石的形态、内容及方位。但由于许多碑刻字迹不清,照片的反差效果不明显,碑文难以识读。参观了几个博物馆的拓片展后,她发现,碑拓是比照片更完美的研究资料。
拓碑是一项古老的技艺,借助宣纸、墨汁、拓包等工具,经过洗碑、上纸、扫纸、椎拓、上墨、揭纸等流程,能将碑石上的文字和图案清晰地复制出来。拓碑看起来简单,但需要长期磨练,技术含量颇高。如今,许多省市已将传拓技艺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亲力亲为地拓碑,尤其是在野外拓碑,对于非专业拓工的师生,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在开展仪式上,她历数“被逼上梁山”自学拓碑的原因:各种法律碑、公文碑拓片因鲜有人问津,没有购买渠道;各大图书馆收藏的老旧碑拓,想一睹真容难之又难,拍照复制手续繁琐,价格高昂;已出版的碑刻文献辑录,与原碑原拓对照,省略、缺漏、错讹比比皆是。迫不得已,为打破珍贵学术资料长期被“垄断”“封锁”的现状,只能自力更生,广开门路,建立为学术共享服务的第一手资料系统。
两年前,李雪梅带着学生拜师习拓。一路摸索下来,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之后,师生的摹拓技术有了明显长进。2015年,一个夏日的傍晚,师生们终于在碑石上拓出了“乌金拓”的效果,一行人忙着拍照留念,结果,错过揭下宣纸的最佳时机,导致纸粘在碑石上难以脱落,最终勉强揭下来的拓纸“跟狗啃的似的”。这一次经历,被李雪梅称为“得意忘形的失败”。
在2015年前,李雪梅和学生外出访碑的工具不过是相机、纸笔、卷尺,着迷于拓碑后,外出访碑又加上宣纸、墨汁、拓包、打刷……行李多了,访碑的乐趣也增加不少。寒来暑往,无论是身处静寂碑林,还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只要能摹拓出清晰的法律碑文,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通过展览传播法律碑刻文化
两年多的拓碑实践,师生间已形成默契的分工。老师和女生主攻蜡拓(干拓),男生钻研墨拓(湿拓),拍摄、绘图、丈量尺寸,也各有专人负责。每每访得“秘籍”中载录的碑刻,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而与碑石摩挲,也就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待到离开时,“一步一回头”,像告别挚友般依依不舍,李雪梅笑着形容他们的访碑常态。两年多时间,他们搜集了数百份历代法律碑拓,其中一半为亲手摹拓。在微信朋友圈,他们的“拓拓”作品时常成为主角。由于学校展厅空间有限,此次全国首次举办的古代法律碑拓展,不过才展示了他们藏品的二十分之一。
访谈中,李雪梅一直在强调分享的快乐。除了以展览的形式分享这些来之不易的学术资料外,平时每得到一张新拓片,她都先不拆封,等到课堂上一起和学生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
中国古代碑石,数量多,种类繁,要从众多碑石中找到法律碑刻,对于李雪梅和她的学生们来说,并非难事。从碑额、行文格式、落款中,她们一眼就能发现那些熟悉的标记。
而从具体内容上看,不同时代的法律碑刻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法文化的源远流长。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说:“法律是庄重的,书写碑文的书法也是庄重的。用庄重的书法书写庄重的法律,表达对法律的敬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李雪梅介绍说:秦汉至隋,为刻石纪法的初创期,“碑以明礼”是主导;到了唐宋金元,碑石上公文众多,体式俱全,“碑以载政”成为鲜明特色;至明清,敕禁碑、官禁碑、民禁碑层出不穷,“碑禁体系”完善,故“碑以示禁”成为时代主流。总体来看,古代法律碑刻具有道器兼备、官民互动、现实救济等特色,其在古代法律文化传承和地方法律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广泛而积极的效用。
在遍访碑刻、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李雪梅写成《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一书,于2016年获北京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此前,她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碑刻法律史料考》获第四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通过言传身教,李雪梅不仅将法律碑刻文化种在了许多学生心里,也使访碑拓碑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最让她欣慰的是,一些学生已从碑石的门外汉,成长为读碑、拓碑的行家里手,而他们所掌握的拓碑技艺,也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有所助益。
通过展览,无疑能够把法律碑刻文化传播得更广。关于未来,李雪梅的设想是,能够将法律碑拓按公文碑、讼案碑等专题进行展出,让更多人更加深入地领略法律碑刻的魅力。
原文链接: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70508/Articel07002G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