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学术圈还是大众知识界,应星的身份都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最近他出版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乍看上去,像是一本历史类著作。其实,应星的这本书是一次将社会学与历史学努力结合的尝试,他将这本书的研究方法称之为“群体传记法”,即依靠历史上多个人物的日记和传记,进行一种群体性的分析,看看历史上曾经鲜活存在,影响历史的人物,他们共同的生活背景是什么,又共同受到了哪些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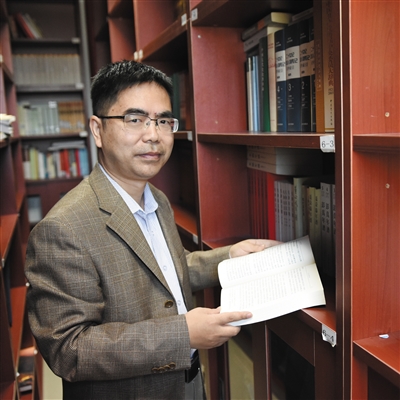
(应星,1968年生,重庆市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
作者:应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5月
“新教育场域”,其实是“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通过三个个案考察,展示从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
这本书虽然出版得较晚,却是应星2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奠定的研究内容。全书虽然研究的是20世纪初科举废除、新式学堂兴起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但其所用的研究方式却是社会学经典的质性研究。
应星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格局,他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为了既没有历史、又没有国家的社会学,社会学者关心的都是社会现实问题,一头扎进一个个村庄或者社区里面,进行田野调查或者口述访谈,而忽视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必须结合国家、政党和历史这些研究维度的。今天社会学的许多经验研究是缺乏经验感的研究,而这种缺失往往就是因为经验现象被人为抽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东西。所谓“不察其渊源,就难以观其流变”,应星多年来一直呼吁将历史重新带入社会学视野中。
纵观应星的学术履历,会发现应星先前的关注焦点一直围绕农村的问题。从2001年围绕三峡移民所写就的《大河移民的上访故事》,到研究改革开放前乡村的伦理秩序;从用“气”解释乡村社会冲突的机理和规则的《“气”与抗争政治》到梳理“三农问题”政策的《农户、集体与国家》。十多年来,应星都被贴上了乡土社会学家的标签。
但应星说,我之所以研究农民和农村,背后的关注点其实是权力。这个权力并不是一般政治学上,国家对人民所使用的权力,也包括人民所进行抗争,由下对上的权力,甚至还包括普通人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在他看来,研究乡土中国,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权力的一个基础,也是可以理解国家机器运作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我的一生都是在‘政治’和‘学术’中不停地交战”
1968年,应星出生于重庆,父母都是重庆大学教师。虽然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但幼小的应星开始并没有对做学问、搞研究产生多少兴趣。或许是因为逆反的心态,应星反而有些瞧不上知识分子的工作,觉得有些小里小气。儿时的应星,梦想的是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过上金戈铁马式的生活。
1985年,应星考上了厦门大学最热门的外贸系,但读了一年就放弃了,主动申请转到最冷门的哲学系。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疯了,先不说学哲学毕业后是否能挣钱,找工作恐怕都非常困难。但应星不在乎,他受了马克思那句名言的影响:“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应星希望可以通过哲学思想来改变社会的现状,实现儿时心中的梦想。
1993年,应星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攻读硕士,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从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志业。他跑到乡村做口述史,对村民做访谈,搜集第一手资料。这样的经历,让出生在城市的应星第一次进入了农村,真切地体验到了农民们的生活方式。
后来,应星来到重庆某县挂职一年。这一年对于他的学术经历有了巨大的冲击。“挂职前,我特别喜欢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为黄土地而奋斗”。但是当他看到了真实的乡村之后,他发现以前从书本上读到的乡村变得极为不真实,自己对农村和农民的理解也都是想象的成分,乡村问题远比书本上写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现在,总觉得某些基层干部非常坏,欺压群众,乱收费。但你通过走访会发现,有些干部其实也是迫于无奈,因为他们在基层的责、权、利是完全失衡的。反过来看农民,他们其实是与基层干部同享一种文化。二者在彼此互动中,其实都参与到了对权力机制的建构中”。
“原来,我很向往用政治家的方式改变农民的命运,但下去之后,我发现我所向往的那种改变力量非常有限。反而社会学研究或许可以间接地将问题揭示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家。”思想意识的改变,也促使应星研究方法的改变。应星开始用“发现”的方式进行他的社会学研究,即把农民生活中最习焉不察的一些话语和生活方式通过学术的分析,赋予一种新的理解。
比如,中国人经常说“人争一口气”。应星就由此发现,“气在乡土中、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现实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动力,是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
在应星看来,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政策性或者实务性的工作,它无法提出现在社会上种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我只是将社会的复杂性揭示和呈现出来。我在农村做口述史,你要说我的书出来之后,是否对当地的现状有所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社会学自有它现实的意义。我相信现在读过我的书的学生,他们未来会有人从政。这些书里面所揭示的复杂问题会贯穿到他们的思想中,在未来,他们作为政治人物会提出具体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几代知识人不断努力,一点点地做出改变。”
或许是由于应星这种客观做学问的态度,让他的社会学研究两头不讨好。农民和基层官员都不满意应星揭示出的二者在权力运作中都存在的问题。“但社会学研究的鼻祖韦伯说过,你的学术研究,就是要能把对立双方都不喜欢的东西呈现出来。”
应星喜欢韦伯,也正是由于韦伯的文章,让他认识到了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对我的一生,可以用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来概括,我的一生其实就是在”学术“和”政治“中不停地交战。”但我现在完全沉静下来了,每天坐在书房里一点点爬梳史料,一点点去做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我觉得这是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它不再是我以前向往的那种轰轰烈烈、一呼百应的影响,但我觉得这种做学问的努力,也许比我以前向往的方式更重要。
■ 对话应星
本土社会学 必须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状态中
新京报:做社会学田野调查,通常都是深入到一个乡村,对那里的村民进行口述访问,然后通过对那个乡村的分析进而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变化。这种研究模式会不会有以偏概全的危险?
应星: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比如费孝通先生写过《江村经济》,国外学者就质疑他,你就是研究一个江村,为什么副标题敢叫“中国农民的生活”?凭什么说江村就是中国的农村?
我觉得我们要研究分析的村庄,一定不能随便找。我反对所谓“家乡社会学”,即社会学者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家乡当作个案分析对象。并不是家乡研究不可以做,而是说你选择家乡作为研究对象,这并不具有自然正当性。你研究的村庄,一定要精心选择,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复杂性和张力。这个村庄所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所牵动的那些人物的命运,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厚度,就像《白鹿原》一样,你通过白鹿村跌宕起伏的命运,理解了乡土中国。只有具有这样的厚度和气韵,你选取的个案才会有意义。
新京报:你这些年来一直强调“本土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究竟应该如何做?
应星:所谓“本土社会学”,并不是与西方社会学相对抗的关系。其实我自己开始受到的熏陶也主要是西学的。我们首先必须要对西方思想有整体理解。不理解西方的现代性,西方的政治,我们也就不可能做好自己的研究。因此,社会学者必须在西方社会理论的学习上下大工夫。但是,了解西方社会,并不等于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直接用。你必须要能够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状态中来。我的研究常常就是要去体会中国社会中一些习焉不察的东西的社会学滋味。比如,我现在在做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就是尝试重新体会中国政治话语里面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些问题的意味,我希望通过分析这些话语重新理解当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这些词里面其实蕴含着中国人在现代的经验和体验,非常真实。
当我们说要努力建构具有中国味道的社会学时,绝不是说我们只要抱持着民粹的情怀到田野中去,进入中国的村庄、工厂和社区就可以了。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恰恰需要对于整个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完整的、长时段的理解。或者说,在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建构中,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的把握恰恰是极其重要的环节。
原文链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6/17/content_685401.htm?div=-1&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